山东历城朱氏与《聊斋志异》
来源:管理员 | 上传者: 中华朱氏网 | 2023/04/23|浏览量:1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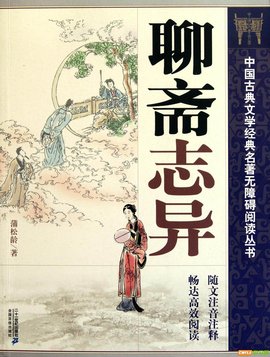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小说之冠冕,三百余年来盛名不衰,从蒲松龄开始创作到“青柯亭”初刻本的出现,历时百年之久。其主要原因在于蒲松龄及其子嗣位卑家贫,无力印行;另外,《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184,在创作方式上打破了传统,文人群体对其由了解到接受尚需时日。《聊斋志异》初次结集是在康熙十八年( 1679) ,其后淄川高珩、唐梦赉,新城王士禛等名人显宦在阅读了部分手稿后都给予高度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聊斋”的阅读风尚,从淄川到济南的文人群体中,《聊斋志异》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并拥有大量的潜在读者。虽然高氏、唐氏、王氏均有家族刻书的传统,但在《聊斋志异》持续创作和初步产生社会影响的阶段,他们显然不可能将之刻印。然而,同样有刻书传统的历城朱氏抄录《聊斋志异》则是在蒲松龄创作的后期,并且从对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态度上看,朱缃与高珩、唐梦赉、王士禛三人相比大为不同。高珩、唐梦赉与蒲松龄之间或为亲戚,或为同乡好友,三人交往频繁、友情深厚,他们都曾为《聊斋志异》写序,是《聊斋志异》最早的读者之一。王士禛则为在朝高官,因为机缘巧合才对蒲松龄有所垂青,更因相同的个人爱好而对《聊斋志异》比较看重。尽管高、王等人对《聊斋志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他们毕竟仅阅读和抄录过该书的部分手稿。而朱缃生于康熙九年( 1670) ,对大他三十岁且已名满济南的蒲松龄倾心仰慕,正是基于对《聊斋志异》的深度理解,他才不惜花费十余年光阴精心抄录和校订,至晚在康熙四十五年( 1706)左右,便将《聊斋志异》全部抄录完成并进行了校正,已经拥有了基本的刻印条件。表面看来,似乎是朱缃于康熙四十六年( 1707) 突然去世导致了《聊斋志异》的刻印工作没有付诸实施,但深入分析后则会发现朱缃似乎并无刻印该书的打算,其子朱宾理、朱翊典在这一点上也与其父高度一致。
一、历城朱氏与《聊斋志异》的渊源
朱缃( 1670—1707) ,字子青,号橡村,山东历城( 今济南市) 人。历城朱氏为当地豪门大族,虽在鳌拜擅权时遭到打击,但在鳌拜覆灭之后家族重振,累有朝廷大员和封疆大吏。朱缃“有隽才,自经史至天官壬遁之书无不研究,尤致力声诗……援例候选主事”[2]636,他不乐仕进,尤爱风雅和交游,为济
南府一代名士,也是王士禛的诗弟子。王士禛《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称其:
少负逸才,自六经、三史、四库、七略,旁及天官、壬遁之书,无弗习。顾薄科举程文,以为不足为, 而独致力于歌诗。其为诗,义兼骚雅,体备文质,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青,彬彬然近代一作手也。子青既 盛有时名,四方胜流名士过历下者,揽湖山之秀,挹泉流之洁,而未识子青,则犹以为未足也,必停车结 驷而造焉。[3]151
王氏极力称赞朱缃的诗,并称其为“近代一作手”,尤对其乐善好客的“名士风采”大加赞赏。而与高珩、唐梦赉、王士禛诸人相比,朱缃对蒲松龄的认识超越了所谓“怜才”“提携”“垂青”等非对称式关系,而是真心倾慕,对《聊斋志异》的创作旨趣也最为理解。其《聊斋志异》题词三首云:
冥搜研北隐墙东,腹笥言泉试不穷。
秋树根旁一披读,灯昏风急雨濛濛。
香茆结就新亭小,睡觉桐荫一欠伸。
君试妄言余妄听,不妨狐窟号诗人。
捃摭成编载一车,诙谐玩世意何如?
山精野鬼纷纷是,不见先生志异书![4]34
其后,朱缃得到了不断借阅和抄录《聊斋志异》书稿的机会。袁世硕先生曾从中山大学所藏“寄聊斋”书札中搜检出四封,认定是朱缃写给蒲松龄的书信,并在详细考辨后认为: 一,朱缃在康熙三十五年底,已经将前时借阅的七册《聊斋志异》抄录后归还; 二,在康熙三十六年夏天,朱缃提出再借抄余下的八册,说明蒲松龄此时已创作完成《聊斋志异》的大部分;三,在康熙四十一年深秋,朱缃提出再借阅十五册之外的部分新作,说明蒲松龄此时虽仍未完全搁笔,但也仅是少量篇章,不会超过一册; 四,在康熙四十五年,朱缃请蒲松龄来济南时顺便将《聊斋志异》书稿全部带来,好对十余年所抄《聊斋志异》进行校正,说明此时十六册《聊斋志异》大体已成,抄本也几近完工; 五,朱缃是最早读完并抄录全书的人。[7]233 - 240
可惜在康熙四十六年,年仅三十八岁的朱缃病故。朱缃有五子,即崇勋( 字彝存) 、崇道( 字带存) 、宾理( 字佐臣) 、翊典( 字佑存) 和瑞宙,朱缃去世时五子年纪尚幼小,未能顶立门户。“查《历城县志》之《选举表》和《貤封表》: 朱崇勋次子琦在乾隆十二年( 1747) 中顺天乡试,授神木县知县; 五子璜在乾隆十八年( 1753) 中山东乡试; 朱崇勋及其父在乾隆十六年( 1751) 因朱琦貤封文林郎神木县知县。据此可知,朱崇勋约在乾隆十八年左右为六十岁,雍正元年( 1723) 为三十岁左右,其父朱缃在康熙四十六年( 1707) 去世时,他仅只十四岁左右。”[7]383,子嗣幼小,当是朱缃《聊斋志异》抄本陆续为人借走而致大部分散佚的重要原因。
后来,朱缃之子再次从蒲家借出《聊斋志异》书稿并进行整本抄录。主要依据,一是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卷末有“殿春亭主人”识语:余家旧有蒲聊斋先生志异钞本,亦不知其何从得。后为人借去传看,竟失所在。每一念及,辄作数日恶; 然亦付之阿閦佛国而已。一日,偶语张仲明世兄。仲明与蒲俱淄人,亲串朋好,稳相浃,遂许为乞原本借钞,当不吝。岁壬寅冬,仲明自淄携稿来,累累巨册,视向所失去数当倍。披之耳目益扩。乃出资觅佣书者亟录之,前后凡十阅月更一岁首,始告竣。中间雠校编次,晷穷晷继,挥汗握冰,不少释。此情虽痴,不大劳顿耶! 书成记此,聊存颠末,并识向来苦辛。倘好事家有欲攫吾米袖石而不得者,可无怪我书悭矣。雍正癸卯秋七月望后二日,殿春亭主人识。[8]746
所谓“殿春亭”即朱氏园亭,朱缃及其孙朱琦的诗中均有载录。既云“余家旧有”,时间又在“雍正癸卯”,即雍正元年,则“殿春亭主人”当为朱缃之子。第二个依据是蒲立德《东谷文集》有一篇预拟的《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其首段云:
右《志异》为卷若干,为篇若干,先大父柳泉公所著,朱君佐臣、佑存两世叔编次,以谋梓行者也。昔,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交无人焉,独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先生以诗名于世,公心赏之; 公所著书才脱稿,而先生亦索取抄录不倦,盖有世所不知而先生独相赏者,后之人莫得而传也。洎公与先生俱谢世,先生嗣君佐臣、佑存皆能世其家学; 而我先人相继沦亡,余小子德抱守故业,多病无成,阐扬无自,然窃谓《志异》一书必传而未必传,非但后人之咎,抑亦我公平生知己之少也。而两世叔深嗜笃好,缮写成篇,且将授梓而刊行焉。[7]382
以“朱君佐臣、佑存两世叔”等语与“殿春亭主人”识语对观,则“殿春亭主人”基本可认定为朱缃的 第三子宾理或第四子翊典。袁世硕先生则认为其“为朱宾理、翊典兄弟偶用之署名。至于执笔撰写识语的,究竟是宾理还是翊典,文献不足,就难于确定了”[7]383。
但是,根据 2008 年 4 月 28 日北京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所拍高凤翰《殿春亭图》手卷作者题款“偶
为叙园老弟写意”及朱岷书引首所署“侄岷为叙园四叔题”等信息可知,“殿春亭主人”当为朱缃四子朱翊典,“佑存”“叙园”当为其字号。尽管“殿春亭主人”的抄本没有留存下来,但幸有历城人张希杰曾据之抄成了著名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二、朱缃未刻《聊斋志异》的缘由
朱缃一生与蒲松龄往来频繁,友谊深厚,是《聊斋志异》的爱好者、抄录者和忠实读者,但他在世时并未将所抄录校订的《聊斋志异》刊刻印行,不免为《聊斋志异》的传播留下了遗憾。
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朱缃抄录《聊斋志异》和保存其抄本的时间在康熙三十二年至康熙四十六年之间,而在此之前的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康熙圣谕云:
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俱宜严行禁止。[9]385
这是继顺治九年( 1652) 题准严禁“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10]165之后,第一次专门发出的皇帝御旨,查禁程度有所加强。当然,所谓的“琐语淫词”或“淫词小说”主要是指猥鄙的情爱作品,也隐及一些所谓“败坏风俗,蛊惑人心”的文言杂著,如清初张潮《虞初新志》就因实录明清易代之际的人、事而遭打压。而纪昀所谓“一书而兼二体”[11]1475的《聊斋志异》在文体类型上是跨界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文人笔记或传奇小说,如高珩、唐梦赉、王士禛等人基本上都目之以文采颇高、兼具志怪和隐喻性质的“古文”作品,与“淫词小说”有很大距离。但是,《聊斋志异》在内容上毕竟有些“离经叛道”、“事涉荒诞”,还偶有诸如隐喻清军杀戮行为、批判科举时弊、讥讽吏治腐败等篇章段落,即便有高珩等人从“有益政教”方面为之张目,但在清前期统治者执行文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也不宜高调传扬。因此,《聊斋志异》在当时能得到高珩、唐梦赉、王士禛、朱缃等人的高度赞誉已非常难得,再进一步刻印推广就有了难度,有刻书传统的高氏、唐氏、王氏也自然均未有此种表示。从有所顾忌方面来说,此时高氏、唐氏均退职居乡,尚不须刻意注重; 但身为朝官的王士禛就不能不特别谨慎,以至于委婉拒绝为《聊斋志异》作序。而朱缃身为巨宦世家之子,即便并未真正出仕而以风雅自命,仅将这部“诙谐玩世”的“山精野鬼”之书全部抄录就已经有些“不务正经”,作为“雅好”则可,而真要将其付梓刻印推而广之,则有违士林正统文人循规蹈矩的习惯,在有着深厚儒学正统根基的山东首府之地也不易被人接受。朱缃抄本后来“为人借去传看,竟失所在”,也间接反映了当时士林文人对《聊斋志异》的态度,至少是不够重视。
其次,明代在刻印各种丛书、类书时往往将前代及本朝的文人笔记和文言小说广为收录,像《太平广记》一类的传奇小说集、《稗史汇编》一类的类书体小说和《语林》一类的世说体小说都蔚然兴盛,而这一现象在清初则辉煌不再。一是易代之乱使文人的消遣之心大减,二是清王朝文化钳制政策与小说禁令密切相关,文人对小说的态度变得较为审慎,即便对文言小说也远不如明中后期那样开明。如清初曹溶辑《学海类编》时对文言小说“概不录入”。这样的“治学”丛书引领了学术风气,对那些言辞“猥鄙”“事涉荒诞”的文言作品自然有所打击。在这种背景下,官刻、私刻均不太注重文言小说。山东主要的刻书世家如新城王氏、曲阜孔氏、淄川高氏等均主要刻印自著诗文、学术作品及经史典籍,偶尔会刻印一些前代的“说部”之作,但对同时代的文言小说则基本持拒绝的态度,即便类似于王士禛《池北偶谈》这样自著自刻的文人笔记类小说也少之又少。
历城朱氏刻书,始于朱昌祚,盛于朱缃,朱缃是第二代刻书者。“六代刻书,自第一代朱昌祚始,至第六代朱汲止,刻书达二十余种”,“刻书内容除朱纲《检尸考要》、朱曾武《四书字意说略》外,余皆为诗文集”[12]126,根本没有外人的作品,更没有文言小说。并且,从《聊斋志异》之《司训》篇末附录的“朱
公子子青耳录云”[13]2181看,朱缃应该著有类似于文人笔记的作品《耳录》。但是,至今不仅未见《耳录》的传本,也没有文献显示其曾经刻印。由此可知朱氏家族在对刻书类型的选择上,是非常审慎的,哪怕是亲著的说部杂书,也不予刻印,至于外人所作、“事涉荒诞”的《聊斋志异》,当然就更不符合朱氏的选刻标准。
第三,朱缃作为一代文人名士,抄录《聊斋志异》更多地是以收藏为目的,对刻印传播则不那么在意。一方面,明清文人有控制小说一类书籍社会影响的传统,尤其是不那么“正规”的作品。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针对《金瓶梅》的抄录和刻印问题即言: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 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
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 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
中悬之国门矣。[14]652
因此,抄本传播虽然低效,但传播的范围可控,它既能让文人友辈共赏奇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影响。朱缃极度喜爱《聊斋志异》,下大力气抄录全本,也借给同好相抄,但不力行刻印,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上述传统的。另一方面,因“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15]151,因此明清很多藏书者往往重视抄本甚于刻本,即便是抄本也要求得其最善者,对说部著作亦如此。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河南邵氏闻见后录三十卷”条即云: “宋人说部,虽有刻本,必取其钞本藏之,恐时刻非出自善本,故弃刻取钞也。
钞本又必求其最善者,故一本不已,又置别本也。”[16]443典型的例子,如清中期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的潘世恩因非常喜爱《儒林外史》,在已经有刻本流布的情况下,又对刻本进行修缮重抄,只为收藏。可见在明清一些文人,尤其是藏书家看来,完美地抄录一部作品的重要性甚至会超过将之刻印推广。朱缃抄本直接录自蒲松龄手稿,抄成后又借手稿加以精校,可谓《聊斋志异》抄本中的最善者,收藏价值自然不言而喻,至于刻印推广则属于可为可不为之事。
第四,限于印刷技术,当时刻印书籍的成本很高,刻书人不会轻易为之。如乾隆五十六年( 1791) ,纪昀奏旨换写《性理大全》,“以每册二、三万字计算,写价已六七两,加以纸价装潢,须八九两方换一册”[17
]2271 - 2272。这是抄本之价,刻本则翻倍。当然,私人刻书的工价会比官刻略低,但刻一套五十余万字的《聊斋志异》书版至少需银三百两,各种物料开支还需几百两,再加上工时、食宿等费用,总计不会少于一千两。这还没有将负责校雠的杭州著名文士余集( 字蓉裳) 、赵起杲胞弟赵起杭( 字皋亭) 、“郁佩先”和负责刻印事物的“陈载周”等人的筹劳计算在内。并且,当时书版一次印刷的承载能力大概也就五十到一百部,效率是比较低的。活字印刷技术虽然早已应用,但问题很多,成本和效果也并不十分理想; 至于不用刻板又经久耐用的石印技术,至 19 世纪中期以后才大量应用。另外,文言小说的读者基本限于文人,以抄本形式在同好之间借阅传抄,虽然范围有限,但终究是一种简便的传播方式。因此,在朱缃所处的时代,没有强大的促动力和适宜的时机,一部文言小说极不容易被刻印。总体上看,在清廷查禁“淫词小说”的社会背景下和重学术轻小说的文化氛围中,朱缃在一定程度上沿承明末清初文人、藏书者有意控制小说社会影响的做法和极重视抄本的藏书传统,对《聊斋志异》重收藏抄本、轻刻印传播,甚至根本就没有将之刻印刊行的打算,在其诗文作品和与蒲松龄的往来信笺中,也未见有关于刻印的只言片语。当然,已经落后的印刷技术和较高的刻印成本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至于朱缃的英年早逝,则恐怕并不是他未刻印《聊斋志异》的重要缘由。
三、朱缃之子未刻《聊斋志异》的缘由
从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卷末“殿春亭主人”“识语”看,朱翊典对朱缃抄录蒲松龄手稿之过程不甚了了,对《聊斋志异》本身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成就也没有评述,强调的主要是对家传抄本“为人借去传看,竟失所在”的痛心疾首,故而不吝代价也要再借原稿重新抄录,“前后凡十阅月更一岁首”,至雍正元年七月中旬抄录完成。“识语”完全没有提及刻印刊行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蒲立德不仅预拟了《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而且还在文中说“右《志异》为卷若干,为篇若干,先大父柳泉公所著,朱君佐臣、佑存两世叔编次,以谋梓行者也”呢?这要从朱翊典借手稿的方式和途径上分析。
朱氏之所以能顺利从淄川蒲家再次借出手稿,主要有三个条件: 一是蒲松龄当年与朱缃有着深厚的忘年之谊。时人中朱缃对《聊斋志异》的理解最为深切,所以蒲立德《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对朱缃有格外的赞言,称“世所不知而先生独相赏”,又称“知之之真而赏之亦真,橡村之外,求复有一橡村,安可得耶?”自然,蒲立德对朱缃之子必然是有所期待的。二是蒲氏与张氏同居缁邑并几代交好,蒲立德与张作哲( 字仲明) 平辈论交,而张作哲因其父张元在朱缃家的馆师地位,与朱宾理、朱翊典兄弟的关系也很好,因此朱翊典会通过张作哲向蒲立德借《聊斋志异》书稿,这里就有了一个信息传递是否确实的问题。三是蒲立德当时已有将《聊斋志异》付梓的迫切愿望,只是因家贫无资故而希望借助外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家族刻书传统、自上代就能对《聊斋志异》整本抄录的朱氏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借力对象。蒲立德作于乾隆四年( 1739)的《〈聊斋志异〉跋》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欧阳而后传; 文长雄踞一时,必待袁中郎而后著。自今而后,焉知无欧阳、中
郎其人者出,将必契赏锓梓,流布于世,不但如今已也。则且跂予望之矣![4]32
对于蒲立德而言,朱翊典有如传昌黎文之欧阳修、扬徐文长之袁宏道,因此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从蒲立德预拟《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可推知张作哲在从蒲立德手中借出书稿时,定会与蒲立德有某种口头约定,或是张作哲为借出手稿而假朱氏之名迎合蒲立德,或是“殿春亭主人”真有刊刻之意,两种可能似乎均存在。
然而,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朱缃在世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在朱翊典长成之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加强查禁淫词小说方面,康熙五十三年,即朱缃逝后第七年,圣谕对造作、刻印、买卖、阅读淫词小说者以及监管失职之官吏量定了处罚标准,后来这些处罚标准收入《大清律例》,并在雍正二年加以重申。因此,就当时看来“事涉荒诞”也有触犯时忌之嫌的《聊斋志异》而言,作为贵胄公子居家欣赏收藏无妨,真要公
开刊刻难免仍不合时宜,并于身份地位有碍。在家族刻书传统方面,朱缃之弟朱纲刻书,所刻皆自著诗文和专著,有《苍雪山房稿》《粤游草》《滇游草》三种康熙刻本和《检尸考要》雍正刻本; 朱缃的长子崇勋、次子崇道也刻书,朱崇勋有《桐荫书屋诗》二 卷,朱 崇 道 有《湖 上 草 堂 诗 》一 卷,均 为 乾 隆 刻本[12]121 - 122; 而号为“殿春亭主人”的朱翊典并未见有书刻印。
既然继承朱缃刻书传统,也即掌管历城朱氏一脉刻书事业的是朱崇勋及朱崇道,那么朱翊典又如何能轻易动用家族资源,刻印一部有些“不合时宜”又曾被轻易外借以致散佚的文言小说呢? 至于对明末清初文人、藏书者有意控制小说社会影响的做法和极重视抄本的藏书传统的沿承,朱缃“世其家学”的几个儿子和他们的父亲相比恐怕也不会有大的区别。因此,朱翊典在通过张作哲向蒲立德借抄《聊斋志异》手稿或副本时,基本没有刻印的打算。况且在朱氏与蒲立德之间,张作哲穿针引线的作用不容轻视,也存在着张作哲虚与委蛇的可能。
“殿春亭主人”“识语”云: “书成记此,聊存颠末,并识向来苦辛。倘好事家有欲攫吾米袖石而不得者,可无怪我书悭矣。”所谓“攫吾米袖石”,已经透露了不轻易外借外传的意思,也间接反映了其重视以抄本藏书而轻视刻印传播的态度,这与其父朱缃的意图比较一致,而与蒲立德《〈聊斋志异〉跋》所谓“人竞传写,远迩借求”和后来赵起杲青柯亭刻本《弁言》所谓“后借钞者众,藏本不能遍应”[4]8的情况判然有别。朱翊典对《聊斋志异》的这种收藏态度,给《聊斋志异》的大范围传播造成了障碍,其再抄本仅能确认者也仅有“历城张希杰”所抄“铸雪斋抄本”一种。直到乾隆三十一年( 1766) ,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大行天下之时,历城朱氏仍无反应,及至道光时期朱氏家道中落后,自然更无刊刻的可能,朱氏抄本也就渐渐散佚了。
朱氏兄弟未刻印《聊斋志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对《聊斋志异》的接受程度远不及朱缃。他们严重低估了《聊斋志异》及其抄本的价值,而仅止于形式上的收藏甚而置之不理,这与历城朱氏家族主要以诗文传家,多出诗人、学者有关。朱缃之后,其子朱崇勋和朱崇道,族侄朱令昭、族孙朱琦等,皆有诗名或文名。如朱崇勋著有《桐阴书屋诗》,鲁鸿为之作序云:
予读其桐阴书屋诗,囊括众美,匠心独运,不事钩章棘句而自见其渊然而光,苍然而秀。盖密古而
有得者之言,非可袭而取,其历久而愈新无疑也,是诚有得乎温之旨者矣。[18]206
相比而言,反倒是与朱氏兄弟关系很好的高凤翰,在雍正元年七月读到《聊斋志异》后即为之作跋并题诗,大加赞叹,其跋云:
余读《聊斋志异》竟,不禁推案起立,浩然而叹曰: 嗟乎! 文人之不可穷有如是夫! 聊斋少负艳才,
牢落名场无所遇,胸填气结,不得已为是书。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 向使聊斋早脱
韝去,奋笔石渠、天禄间,为一代史局大作手,岂暇作此郁郁语,托街谈巷议,以自写其胸中磊块诙奇哉!文士失职而志不平,毋亦当事者之责也。后有读者,苟具心眼,当与予同慨矣。[4]31
其题诗云:
庭梧叶老秋声干,庭花月黑秋阴寒。聊斋一卷破岑寂,灯光变绿秋窗前。搜神、洞冥常惯见,胡为
对此生辛酸? 呜呼! 今乃知先生生抱奇才不见用,雕空镂影摧心肝。不堪悲愤向人说,呵壁自问灵均
天。不然庐家冢内黄金碗,邻舍桑根白玉环,亦复何与君家事,长篇短札劳千言? 忆昔见君正寥落,丰颐
虽好多愁颜。弹指响终二十载,亦与异物成周旋。不知相逢九地下,新鬼旧鬼谁烦冤? 须臾月堕风生
树,一杯酹君如有悟。投枕灭烛与君别,黑塞青林君何处?[4]35
所谓“寓意之言,十固八九”“胸中磊块”“不堪悲愤向人说”诸语,均为知音之言,比之早年朱缃的题词也更深入一层。朱翊典虽能再行抄录《聊斋志异》,却并无此等胸襟识见。当然,此时翊典诸人年纪不过二十余岁,生活优渥,人生阅历尚浅,也未经举业摧残,因而对《聊斋志异》少有共鸣。反观高凤翰,其祖务农,其父止步于举人,他本人也在科举路上历经磨难,“十九岁考中秀才,二十至四十五岁四赴乡试而不中”[20]1,他读《聊斋志异》抄本,正是在屡试不中的人生阶段,自然对蒲松龄的人生产生共鸣,对《聊斋志异》有所认同。另外,高凤翰早在十五六岁时曾亲见已至暮年的蒲松龄,正如其题诗所言: “忆昔见君正寥落,风颐虽好多愁颜”,“愁”字入骨,准确捕捉了蒲松龄当时的精神风貌,这些都是朱氏兄弟做不到的,以此可以反衬出朱氏兄弟忽视《聊斋志异》社会价值和艺术成就的关键所在。
总之,在清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山东历城朱缃及其子虽然先后两次不惜经年累月全本抄录《聊斋志异》,但是在清廷查禁“淫词小说”的社会背景下和重学术轻小说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沿承明末清初文人、藏书者有意控制小说社会影响的做法和极重视抄本的藏书传统,始终对《聊斋志异》采取重收藏抄本、轻刻印传播的态度。朱缃生时尚能凭借对《聊斋志异》的深刻了解,体察蒲松龄悲愤著文的迂曲所在,领略作品杰出的文学魅力; 但朱缃之子因文学正统观念、阅历较浅等缘由严重低估了《聊斋志异》的价值,长子朱崇勋、次子朱崇道坐令朱缃抄本零落散佚,四子朱翊典虽痛心于朱缃抄本的散佚而重新抄录,出发点却主要是为重拾乃父盛举而重新收藏。因此朱氏两代均未能在《聊斋志异》传播的早期阶段,抓住时机,利用家族刻书的便利条件将之刊刻印行,放弃了加速传播这部杰作的重要机会。后来的“铸雪斋抄本”虽然源自朱翊典的抄本,但其原抄本湮没无存,也没有发现这个抄本与其他抄本、刻本之间的确切渊源。因此公允地说,朱氏两代虽然对《聊斋志异》的早期保存和传播功不可没,但对其刻印以促进更大范围的传播却并未发挥用。
(信息来源:网络,注释省略,编辑部转换,仅供参考,引用请查考原文。作者,张兵郑炜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华朱氏网
2023年4月23日
(有事找站长,支持中华朱氏网,长按扫码)
寻根问祖,查找家谱,就上朱氏家谱库,联系微信:19819884266。

寻根问祖、编修家谱,传播朱氏文化,品“中华朱氏酒”、“朱府囍酒”。金世佳和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华情,19819884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