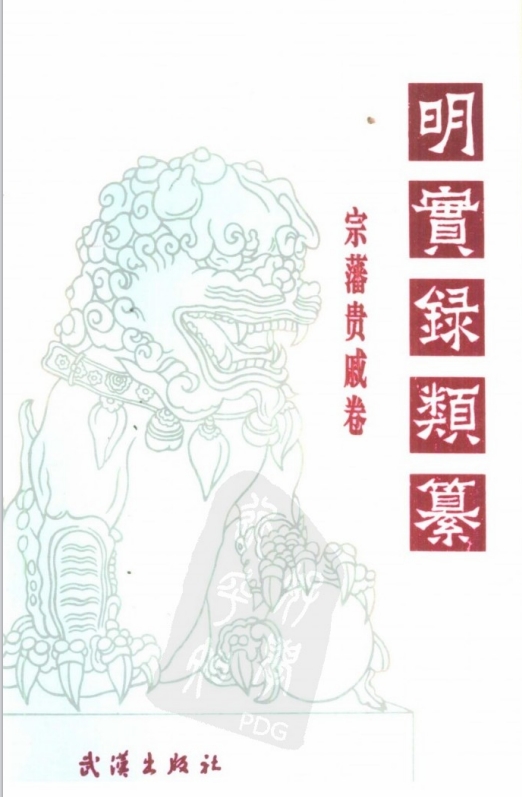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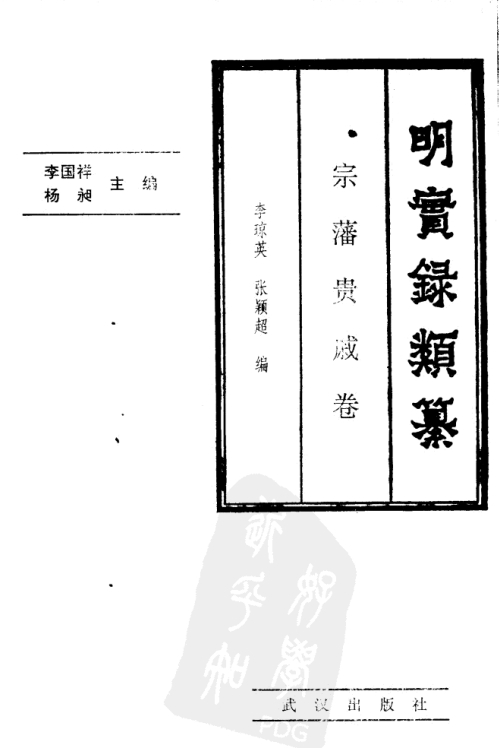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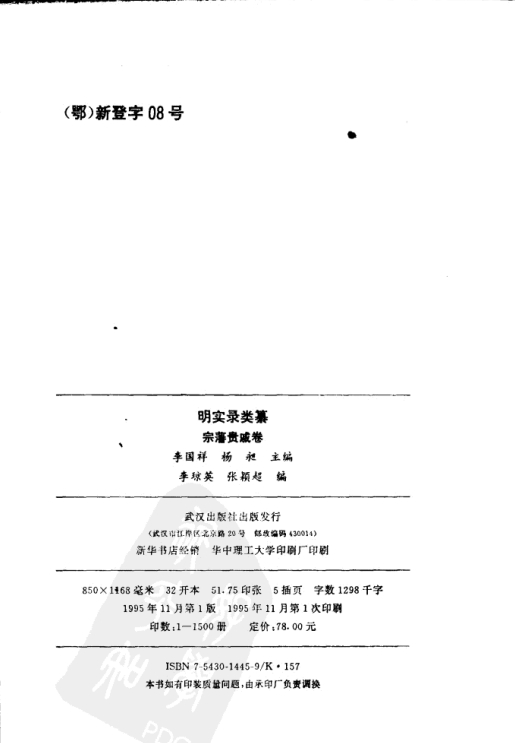
《明实录》及其整理概述
(序言)
有明一代的编年体史料长编《明实录》,凡二千九百二十五卷,一千六百余万字,由明历朝史官胡广等纂修而成。这一鸿篇巨制,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
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源诸夏商;逮及两汉,臻于完备。汉代以降,历朝都有史官专司记录皇帝每日言行,称作“起居注”。唐代,始有宰相自撰“时政记”;宪宗时,又令史官逐日撰写有关朝政事务的“日历”,亦称“日录”。宋以后,更命著作郎,藉起居注、时政记编纂“日历”。起居注和日历均为纂修实录的准备阶段,实录修成后,其书亦即焚毁。然而,此前南北朝梁时,已有载籍题作“实录”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梁皇·帝实录》五卷,梁中书郎谢吴撰,记元帝事。”可惜二书早佚,内容体例均无可考。自唐设史馆开始,凡新君即位,就要敕令史臣以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录等书为依据,加以汇总损益,纂修一部前一皇帝的编年史,称为“实录”。此例一开,历朝递修实录便成定制。实录由于庋藏宫府,卷帙浩繁,本不易行之久远,况且改朝换代,兵燹交加,遂使实录亡佚残缺者不可胜计。当今能全部为世人所见的实录,惟《明实录》、《清实录》二部而已。
明沿旧制,设翰林院,置修撰、编修、检讨等史官,负责纂修国史。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又建立起颇为完备的官方档案收藏保存制度:凡起居注,“纪言纪事,藏之金匮,是为实录”;“凡诸钦录圣旨及奏事簿籍,纪载时政,可以垂法后世者”,都按照会要体例,以类相从,条录成书,叫做“钦录簿”,由各台、省、府设置铜柜,分别储存(《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77)。一俟新君嗣位,辄敕命勋臣充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督率翰林史官凭藉这些档案资料,纂修先君实录。实录修成之后,依例精钞正副两本。正本原藏宫内,嘉靖年间皇史宬建成后,正本遂移存于皇史宬。副本则藏内阁,掌于翰林院典籍。实录底稿随即于太液池畔焚毁,以示禁密。明代二百多年中,先后纂修了自太祖至熹宗共十五朝十三部实录(建文朝附于《太祖实录》、景泰朝附于《英宗实录》),近三千卷。此外,另有《崇祯实录》十七卷,著者不明;而《崇祯长编》,则是清初纂修《明史》时补辑的,现存残本不足七十卷。
实录作为一代官方史料总汇,其体例较为严密、完善,其内容异常浩繁。《明实录》与历代实录一样,体裁系编年体史料“长编”,年经月纬,将重要事件分别归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但于书历朝肇始之首卷时,多追记皇帝继统前行事;载藩王、大臣之死时,则附记其小传于次。《明实录》包罗宏富,凡涉及历史事件、政治设施、军事行动、经济措施、中外交往、民族关系、自然灾祥、社会现状,乃至帝王婚丧、生子命名、祭祀、营造等等,都有详细记录;从诏令奏议、百司重要案牍到人物生平事迹,也要选载。这样完整丰富的资料保存至今,对史学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明实录》在纂修过程中和成书以后,明清两代史家曾纷纷加以评论,《明实录》的价值,言人人殊。贬抑者,则指责它取材但凭吏牍,立传但纪迁擢,内容支离琐碎,轻重失宜,掩非饰过,曲笔良多,甚至斥为无史;尊信者,则“于有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表示对它不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云云。平心而论,《明实录》所记史事、所录材料,既有宫廷和政府各部门的档案作为依据,又有史馆编纂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为底本,尤其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一般都有准确的记录,因此,其史料价值自然较一般记载为高。清初修《明史》,资料多以它为根据,不是没有道理的。《明史》在二十四部“正史”之中,可称上乘之作。然而,清修《明史》,凡涉及清朝祖先的事迹,大都隐讳不书,以示与明统治者无从属关系。《明实录》记载边疆少数民族,据事直书,就材料的真实性来说,的确较《明史》为胜。如明统治者封授女真族的建州三卫以及历次战争与开通马市等交往史实,《明实录》均记载详明;又朝鲜李朝实录亦录有与女真各部的接触关系,二书中保存了丰富的有关清室先世的资料,都为清代官书所讳言或语焉不详者。近人孟心史(森)先生据此二书,纂为《明元清系通纪》一书,已刊十六巨册,书未成而孟氏卒,但清室先世的史实,以此大白于天下。又如《明实录》所载朱元璋北伐檄文,如此重要的文件,不仅《明史》本纪不收,就连毕沅《续资治通鉴》、陈鹤《明纪》和夏燮《明通鉴》,因惧怕触犯清朝忌讳,也都没有载录。这些都足以说明实录的史料价值之高。勿庸讳言,《明实录》作为官修的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史书,必然存在着许多缺陷。自朱元璋兴文字狱起;明朝统治者对封建文化多采取严厉的控制政策,文网甚密。官员士人每因片言只字忤旨犯讳,而获重谴罹横祸;史官纂修实录,自然扬美隐恶,曲笔回护,更助长了实录不实的弊病。李建泰曾批评说:“《实录》所记,止书美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名山藏序》)特别在新君即位不合封建礼法的情况下,纂修前朝实录时便极力掩盖事情的真相,使得新旧交替之际的记载失实更甚。《太祖实录》,在永乐年间曾数度修改,明成祖的帝位本由纂夺而来,修改实录的目的在于预示太祖原有传位于彼之意图,甚至否认其生母而强作马后之子。可知重修的《太祖实录》,讳饰之处颇多;且旧本已被焚毁,所存者惟有最后修订之本,给后世史家留下了不少疑案。英宗复辟以后的情况也是如此,“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至于《光宗实录》,因阉党与东林党的政治斗争而被修改,故歪曲事实之处屡见。又每因史官缺少史德,阿附权势,如焦芳等人谄事太监刘谨,任情好恶,颠倒是非,也使得记载失实。因此,对于实录材料的利用,必须审慎鉴别。
《明实录》虽带有官修史书无法避免的通弊,但它毕竟是经过整理编纂而成的明代历史基本资料,而且首尾完整,载录浩博,事项赅备,可视为一部研究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必须凭籍的重要文献。自昔及今,海内外已有不少善于运用实录史料的范例。清初史学家万斯同,自述当日研治明史:“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方苞《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后他以《明实录》为主要依据,历十余年修成《明史稿》五百卷。他说:“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同上)又清修《明史》时,曾分类摘钞《明实录》,如潘耒修《食货志》,即钞《明实录》有关材料为数十巨册。当代,日本学者采用孟森《明元清系通纪》的方法,编成《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钞》,香港学者编成《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台湾则有《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等。在我国大陆,对《明实录》史料的利用也很重视,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联合纂辑的《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钞》,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合编的《明实录藏族史料》,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的《明实录贵州史料辑录》。此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鹤声、郑一钧编)之中也辑录了大量《明实录》的记载。不少学者运用《明实录》提供的资料,写出了明史研究论著,如郑一钧著的《论郑和下西洋》,杨旸等编著的《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等等。古今中外学者的成功经验,使人们感到进一步整理《明实录》的必要性。如陈高华、陈智超先生主张把这部有重要价值的基本史籍“分门别类,收录汇辑,可以构成比较完备而有系统的专题史料。”(《中国古代史料学》)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在刊行校印本《明实录》时强调,以后该做的工作包括分类整理《实录》,认为“这一类书籍,对研究明代历史的人是很有用处的。”(《校印明实录序》)
近年来,我们在整理研究历史文献的实践中也产生了与陈、黄诸先生同样的认识。我们参与对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的文集进行校注时,曾大量利用《明实录》的史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可通过《勉行集》(杨昶著,武汉出版社1989年1月版)的《〈张居正集>书牍题名笺证》而窥见一斑;笺证《张居正集》有关疑难问题,都是征引了《明实录》后才得以解决的。然而,《明实录》浩繁的卷帙使我们苦于翻检之艰,由此便萌生了分类汇编《明实录》的设想。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及时地给我们以肯定和支持,使这一项目得以实施。经过编纂者们数年的艰辛工作,将近三千卷《明实录》制成了资料卡片并开始陆续纂辑成编。
这一项目,我们原拟编为《〈明实录>地方资料汇编》和《〈明实录>史料分类汇编》两个系列,各包括若干分册。《地方资料汇编》以现今全国三十一个行政区划为准,自成系统,按经济、政治、军事、文教、人物、灾异、交通等事目排比资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纂成一分册;《史料分类汇编》则以宫府朝廷、中外关系、人物传记、地理沿革、战争、刑法、礼乐、选举、宗教等事项为准,分门别类,各自构成专题史料分册。后征求武汉出版社的意见,我们决定以《明实录类纂》统摄之,每一分册则称“卷”。“类纂”之名称,固与“史料分类汇编”指归于一,亦与“地方资料汇编”并无抵牾,所以题作《明实录类纂》统摄之,每一分册则称“卷”。“类纂”之名称,固与“史料分类汇编”指归于一,亦与“地方资料汇编”并无抵牾,所以,题作《明实录类纂》可谓名符其实。分册作“卷”,意在强调《明实录类纂》为一个整体,各卷自成一书又互相关联,条条块块,相辅相成,构筑明代社会的全方位轮廓。
《明实录类纂》是一种史料性质的丛书,为保存史料的本来面目,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只作标点和必要的校订工作,对资料的内容不作改动。为方便印刷,原文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至于资料中不可避免的封建主义糟粕;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造成的,在此提请读者使用时辨识,以定弃取。
《明实录类纂》在酝酿和编纂过程中,一直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关心。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拨出专项资金加以赞助。武汉出版社副总编辑洪源同志负责本书终审,一编室主任余汉康同志承担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工作,他们不辞辛苦,多次登门商讨编纂出版事宜。湖北人民出版社卫侠夫同志扶病拨冗,尽心为本书作了封面装帧设计。另外,武汉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历史系的不少同志,对本书的编纂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协助。在此,我们谨致以深切的谢忱。
我们作为《明实录类纂》的主编人和编纂者,在编纂工作中备尝其中甘苦,深知编成这部大型资料丛书决非易事。加之缺乏经验,对明史的研习尚疏,一些问题考虑得还不周全,尤其是事项的分类,可能挂一漏万,贻笑方家。《明实录》是明代史料的渊薮,我们这部《类纂》是一面纂辑整理,一面编定各卷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热诚盼望专家学者和各位同好不吝赐教,以逐步完善此项工作。
李国祥 杨昶
1989年12月于桂子山
(信息来源:网络)
2024年1月27日转发











